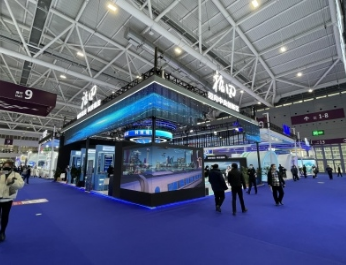雄浑的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矗立在内蒙古高原南缘。这道山脉是我国2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标志性山脉、季风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黄河外流区与内蒙古高原内流区的分水岭,也是内蒙古草原牧区与河套平原灌溉农业区的生态分界线。阴山山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活动在其南北两侧的古代人群的经济与文化差异,也见证了阴山南麓及河套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光(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阴山作为地理界标在考古学和文化史上的意义
阴山一带是考古学者佟柱臣提出的我国大陆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阴山山脉,秦岭-桐柏山-汉水-淮河,南岭-武夷山)之一,属于北方狩猎经济文化与南方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经济文化的接触地带。近年发现的裕民文化(距今约8400年—7600年),就分布于阴山山脉东段北麓草原的山地丘陵地带,其经济形态以采集、狩猎为主,兼有原始种植,考古学文化接触地带的特征突出。
阴山也是考古学者童恩正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组成部分,这一地带自大兴安岭经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延绵至横断山脉,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直是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
阴山还处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这一地带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延伸至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考古学者林沄认为,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这一地带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长期交融的核心区域,其经济形态时农时牧或农牧交错,不断发生变化。
作为我国自然地理的重要一环,阴山山脉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
河套阴山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早期脉络
在历史长河中,阴山山脉很早就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融之地。
据考古确认,早在远古时期,阴山地区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在地球全新世暖期的“盛期”(距今7200年—6000年)到来之际,中原农业居民北上至阴山以南从事旱作农业,成为河套地区的早期农人。
根据考古学者魏坚的研究,在新石器时代,河套地区先后出现了白泥窑文化、庙子沟文化、阿善文化、永兴店文化、朱开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此外还有与白泥窑文化同时的石虎山类型,以及与永兴店早期文化并行发展的老虎山文化。
尽管目前对于河套阴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渊源、性质和发展序列还存在不同认识,但能够确认,河套阴山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在不同阶段受到中原地区后岗一期文化居民、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居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居民持续北上的影响,同时也包括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因素影响。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灰陶蛇纹鬲。内蒙古博物院藏
上世纪70至80年代,河套阴山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遗存出土了环首刀、短剑等北方系青铜器,该文化是主要分布在陕西北部的李家崖文化(有学者认为是鬼方或白狄)的重要源头。上世纪90年代,商代晚期至周代早期的西岔文化遗存出土了管銎战斧等北方系青铜器,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土方遗存。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在准格尔旗——和林格尔丘陵区以南,以西麻青墓地为代表的狄人遗存则明显受到周文化的影响。
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套阴山地区夏商至春秋中期的考古遗存大多与戎狄有关,同时与中原地区也存在密切联系,可谓“半是华夏半戎狄”。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环首剑、环首刀。来源: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
河套阴山地区考古发现的包头市西园、杭锦旗桃红巴拉、乌拉特后旗呼鲁斯太、凉城县毛庆沟等春秋晚期至战国墓地,成为讨论我国北方游牧业起源和匈奴起源的重要材料。这些墓地主要有以下特征:多见流行带扣、S形带饰、斯基泰式短剑、鹤嘴锄等北方系青铜器;普遍殉牲,反映了重视畜牧业的文化传统;墓中常有骨弓弭与骨镞、铜镞,说明对这种武器的重视;墓中多见铜质或骨质的马衔、马镳,而缺乏车器,说明骑马术的存在。考古学者杨建华认为,“以马和羊为主”的殉牲丧葬习俗表明,当时在内蒙古西部等水源稀少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游牧经济。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将中原郡县的居民大规模迁徙至河套阴山地区,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史记·匈奴列传》),“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武帝纪》),“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西汉王朝从武帝开始,在北方边疆设置属国以安置匈奴降众,西河属国、上郡属国即位于河套地区;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入居光禄塞下。东汉时期,匈奴南单于入居西河郡,乌桓入居塞内,拓跋鲜卑也在东汉晚期南迁“匈奴故地”,不断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河套阴山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考古学者苏秉琦指出,距今六千年至四五千年间,自关中西部经渭河、黄河、汾河北上,分别延伸至内蒙古河曲地区、辽西老哈河及大凌河流域的“Y”字形地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他以“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的诗句称颂河套阴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早期阶段,阴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山脉,就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来讲,秦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阴山是秦王朝的北方边界,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民族过程中开始文化转型的地理界标和记忆地标。如北周李贤墓志有“十世祖俟地归……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计,凿石开路,南越阴山……建国拓跋,因以为氏”的记载,又如《晋书》中陇西鲜卑也有“自漠北南出大阴山”的历史记忆。
在“大一统”王朝背景下,中原文化向包括河套阴山在内的边疆地区不断扩展,中原人群也因此扩大了生活空间;而边疆地区在接受中央王朝政治社会制度,以及中原地区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在此双向互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以强化。
河套阴山地区是民族交融互动的舞台
阴山是大规模农业区分布的北界线,同时也是典型游牧文化区的南界线。比如,先秦时期戎狄、秦汉时期郡县居民分布的北界线不超过阴山山脉。阴山还可以视为一条文化地理的分界线。以地理界标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界线、族群地理界线、文化地理界线的多重叠加、交织与互动、发酵,是河套阴山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的原因。
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写到,“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充分说明了河套阴山地区在民族关系方面发挥的调和作用。由于边疆在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方面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河套阴山地区起到了文化缓冲带、民族互动等方面的作用。如,乌兰察布盟凉城县毛庆沟墓地游牧人群与从中原北上的居民葬俗迥然有别,却同处一个墓地,即是河套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例证。
此外,河套阴山的地理区位兼具辐凑与放射、吸纳与发散的文化势能。从文化放射性、发散性角度来说,以朱开沟文化为例,据考古学者王立新研究,该文化向南与晋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均存在交流,向东对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海河流域的大坨头文化产生影响,朱开沟遗址出土的蛇纹鬲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也有分布。朱开沟文化之后,除部分因素被西岔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继承之外,具有该文化独特风格的带领鼓腹肥袋足鬲及其口沿的花边装饰在中国北方地区也得以广泛流布。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鲜卑自盛乐、平城而洛阳的发展历程,则更具说服力。
翦伯赞曾将内蒙古比喻为“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那么河套阴山地区大概可以称为这座舞台上灯光聚焦的中央。如果将自成地理单元的阴山河套地区比喻为中华民族生活的诸多院落之一,那么这座院落坐北朝南,阴山就是院落的北墙,阴山中的孔道就是开在北墙上的门户,秦代的“高阙”或可以比喻为院落的北大门。总之,河套阴山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早期阶段的贡献和意义,值得民族学、考古学和边疆学等研究领域多加关注。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号LSYZD21018)阶段性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海宁
制作 |章音頔
来源 |中国民族报
看完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