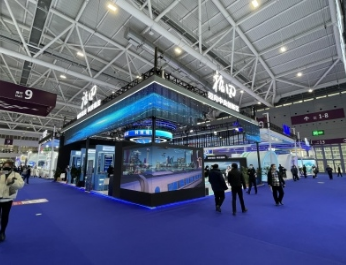“在德不在险”这句名言在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德”与“险”的关系究竟蕴含着何种深意?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长久以来,“德”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它不仅能够超越山河天险,甚至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正因如此,我们在古籍中频繁看到“在德不在险”的各种变体表述。例如,《史记》记载,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洞悉其野心,回应“在德不在鼎”;又如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有一篇批判当时社会盛行的鬼神迷信,结论仅有一句话:“在德不在祀”,意在表明依靠祭祀鬼神消灾祈福毫无作用,唯有修德才是正途。
类似说法还有很多,如“在德不在瑞”,强调祥瑞意义不大,修德才是首要;甚至“在德不在星”,指出占星术在“德”面前毫无价值。
在所有这些说法中,最能将“羲河对话”精神发扬光大的,当属《盐铁论》的第五十章——《险固》。
《盐铁论》堪称一部会议纪要。汉武帝时期,经济学家桑弘羊大力推行改革,旨在增加朝廷财政收入。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增收呢?主要办法有两个:其一,对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禁止私营,依靠垄断获取财富;其二,增加民间经济的赋税,民间经济实体在皇权面前毫无议价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在支持者眼中,这是富国强兵之道;而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财聚则民散”。等到汉武帝驾崩,汉昭帝继位,是否继续推行桑弘羊的改革政策?双方已然剑拔弩张,争执不下。于是,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京城长安召开了一场盐铁会议,让两派展开充分辩论,期望真理能越辩越明。改革派以桑弘羊为首,保守派则是一群儒家知识分子,双方就政治经济方面的几十个主题展开激烈辩论,气氛火药味十足。
到了汉宣帝时代,桓宽整理档案,总结盐铁会议的精神,写成名著《盐铁论》。然而,桓宽本人出身儒家,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明显偏袒保守派。
仅看《盐铁论》的《险固》这一章,先是桑弘羊发言,阐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他大致意思是,只有加强边防,国家才能国泰民安,这就如同普通人家总要修缮院墙一样,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无疑缺乏常识。
保守派则旗帜鲜明地反驳,其内容与“西河对话”高度一致。他们先以秦朝灭亡为例,认为即便拥有金城汤池、兵强马壮,也未必有用,也就是说,修缮院墙作用不大。若真想防备敌人,就应以正义为先,以道德为堡垒。国家有贤能之人,就如同拥有重兵;有贤才,就如同拥有坚固守备,任谁都难以进犯。
桑弘羊心有不服,继续辩解道,自古以来,建国立业皆需依傍山河险阻,占据天时地利,同时还要修筑城墙、挖掘壕沟。
保守派对其观点嗤之以鼻,反驳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 周朝建国,依靠的并非地利,而是人和。反观那些一味依赖地利的国家,无一不走向灭亡,这无疑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桑弘羊一方亦会迅速援引儒家经典,引用《易经》名言“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强调加强防御以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性。
而保守派为捍卫自身立场,竟反驳《易经》观点,称诸侯的城防建设,犹如平民拥有爵位和俸禄,是战国时代才兴起的新事物,是战乱的征兆,绝非太平盛世的景象。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谁也未能说服对方。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看待问题,便不难发现,双方因胜负欲过强,各自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地利与人和并非相互矛盾,完全可以相辅相成。
这个问题在司马光时代依旧意义重大,甚至依旧无法被平和地探讨,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保守派一直将王安石视为桑弘羊第二,那么桑弘羊所支持的,自然就成了正人君子所反对的。
仔细揣摩桑弘羊所表达的观点,在他看来,地利不仅意味着山河险阻,还需辅以人工修建的防御工事。虽说此举必然劳民伤财,但却势在必行。因此,朝廷必须认真理财,增加收入。
在司马光时代,若要反驳上述观点,所依据的思想武器依旧是“在德不在险”的逻辑,前有吴起的相关立论,后有《盐铁论》里儒家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阐发。宋朝人对这些历史经验运用自如。比如筹备修缮都城城墙时,“在德不在险”的论调便频繁出现,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尤其是在讨论修缮瓮城时,反对声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瓮城是围绕城门修建的半圆形防御工事,因其形状而得名,其作用是增强城门一带的防御能力。宋代官员范祖禹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瓮城应出现在边境防御,堂堂开封作为首都,若修建多个瓮城,实在有失体统。开封新城由周世宗柴荣修建,宋太祖在此建都已130多年。此地并无山河险阻,国家只能依靠修德、用人、得民心来稳固根基。
这位提出意见的范祖禹并非迂腐儒生,他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得力助手。在书局默默耕耘15年,《资治通鉴》中唐史和五代史部分,范祖禹功不可没。后来,范祖禹又独自撰写了《唐鉴》,从唐朝300年的历史中探寻成败得失,见解深刻,备受推崇,他也因此被尊称为“唐鉴公”。正是这样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基于“以史为鉴”的理念,援引吴起“在德不在险”的观点,不建议宋朝政府修缮城墙。
事实上,宋朝开国之初,鉴于晚唐与五代的历史教训,便主动拆毁了不少城墙。县城城墙为何被拆?实则是为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再度出现。
宋朝并非首个有此类举措的朝代,早在秦朝统一全国后,便开始四处拆除城墙,这在贾谊的《过秦论》中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一条规律:但凡意图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城市建设方面都会秉持“强干弱枝”的理念。宋朝重修首都城墙、加强卫城建设,意在“强干”;而拆毁各地城墙,则是为了“弱枝”。究竟是修还是拆,考量都颇为务实,并不像范祖禹那般,被政治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脑。宋朝边防力量薄弱,或多或少与这种政治纲领有关。边境地带的城墙拆了又修,反复折腾。
范祖禹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史学家,却缺乏实际政务经验,议论时政难免流于纸上谈兵。所谓“在德不在险”,当内地城池城墙尽毁、无险可守时,虽最大程度规避了地方割据的风险,但极易滋生治安隐患。
《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首任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在宋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这位真实的王伦在山东兴风作浪,带领手下横行无忌,四处劫掠州县。像王伦这样的强盗头子不止一个,他们之所以能肆意妄为,正是因为大宋王朝秉持“在德不在险”的理念,内地城墙几乎拆光,兵力部署也极为薄弱。
不过,司马光与范祖禹不同,他拥有丰富的实际政务经验,因此建议朝廷恢复内地筑城,只需城池规模不大、高度适中即可,如此既不会劳民伤财,又便于防范盗匪。
从司马光的奏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在德不在险”这一观点的态度颇为复杂。实际上只要抛开对王安石变法的厌恶情绪,“德”与“险”的关系本可十分简单。明朝的李濂曾撰写过一篇《宋都汴论》,探讨宋代这段历史,他认为“德”与“险”本是相辅相成的,实在没必要搞得水火不容。在儒家经典里,《易经》曾提及“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山河与城池皆是国防的必要元素。《周礼》中有“司险”这一官职,专门掌管山川险阻相关事务,这是儒家知识分子都应读过的内容,本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却争论了这么多年,着实有些荒唐。
熊逸老师对“德”与“险”关系的解读,带我们穿梭于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从古代诸多“在德不在险”的表述,到《盐铁论》里的激烈交锋,再到宋朝因这一理念引发的种种举措与后果,我们看到了“德”与“险”的关系在漫长岁月里被反复探讨与实践。
其实,正如明朝李濂所言,也如《易经》中“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以及《周礼》设置“司险”官职所表明的那样,“德”与“险”本就是相辅相成的简单道理。山河险阻与道德人心,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国家稳固的基石。
然而,历史上关于“德”与“险”的争论却常常走向极端。究其根源,政治因素的掺杂难辞其咎。各方为了政治立场、利益诉求或不同的治国理念,固执己见,将本应和谐统一的两者割裂开来。
如今,我们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回望,应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在当下,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个人发展,都需平衡“德”与“险”。既要重视道德的引领与凝聚作用,也要懂得合理利用客观条件,构建坚实的保障。如此,我们才能在前行的道路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稳健地迈向更美好的未来。